
(点击图片进入报道专题)
人
物
简
介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自20世纪90年代起,专注于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30多年来,出版《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6卷)、《重回1500—1800——西方崛起时代的中国元素》、《天下中国——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范式》、《望东方——从古希腊到1800年的西方中国报告》(3卷)、《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4卷)、《丝绸之路全史》(2卷)、《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孔子的世界——儒家文化的世界价值》等专著数十部。

· 应该把中华文化放到更广阔的世界文明的坐标中去审视,这样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可以更深刻、全面
· 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来自我们对自身悠久历史文明的认识和体会,也来自对我们的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贡献的了解和认识,来自对中华文明的世界形象的了解和认识
·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东西方一直互相寻找、了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 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态势、文化传播和输入机制
川观新闻记者 王国平 摄影 韦维
中华文化为何能走向世界?
“在世界文明整体格局中,中华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领先,而是整体性的领先。”
“回望”中华文化,为何需要世界视角?
“从这个方面、这个角度去认识中华文化,就会更全面、更深刻,也更能了解我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
在武斌位于沈阳的书房里,对于记者的这两个问题,他如此回答。
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外部世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武斌对“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这一课题潜心研究了30多年,一大批著作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更开辟了观察中华文化的新维度。
“回顾中华民族先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历史,我们会时时感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也是一个跌宕起伏、开拓创新的思想历程。其中,蕴含着我们民族开放谦逊的美德,也锻造着民族文化博大的包容精神。”武斌说,通过对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影响的认识,会更加坚定我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心,增强在新时代发展民族文化、担当推动世界文化发展使命的自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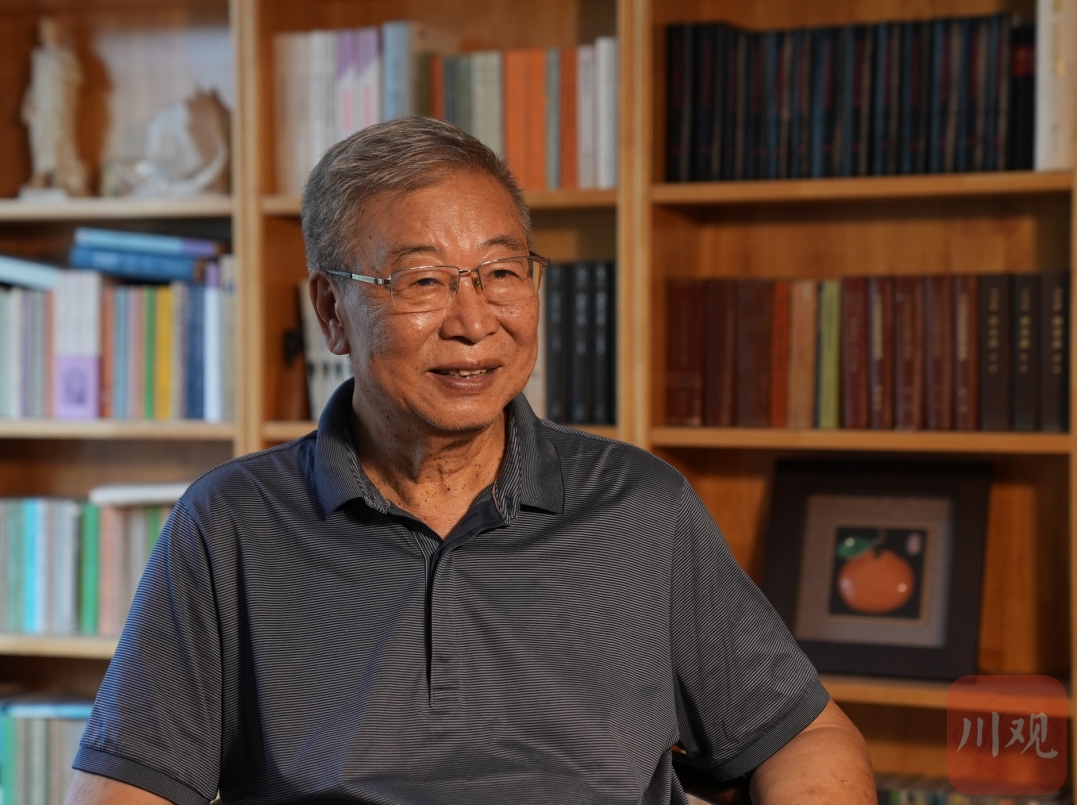
武斌
一次偶然约稿 发现一座学术富矿
虽然主业是研究中华文化,但武斌最初学的是哲学。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武斌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武斌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他最开始研究的是西方哲学史,并小有成果,先后出版了《性灵之光——西方大哲学家轶事》《中外哲学家辞典》《哲学传奇》等书。
彼时,思想敏锐的武斌注意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文化迎来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如何面对现实生活,服务社会实践,这是当时对我们青年学者的时代要求。”武斌说,学哲学的目的,不是都要去当哲学家,都去研究康德、黑格尔,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想明白,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具体工作,都要搞清楚面对的客观事物是什么;其次,想明白了还要说明白。”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武斌从西方哲学纯粹的学术研究转向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并于1991年出版专著《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在这本书中,武斌试图寻找中国人的历史方位以及剖析20世纪对中国人的塑造、中国人对20世纪的接受与回应,他用这种方式解读转折时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在这一过程中,一家出版社向武斌约写一本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书稿。“当时我就想,爱国主义教育应该从哪个角度讲,按照传统的思路,从古到今这么讲下来也可以。”武斌说,“但我想写出新意。”
于是,“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影响”在武斌构思中逐渐成型,“爱国,首先是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文化,我就想到如何从外部视角让读者了解中华文化。”
“想明白”了这个题目,还要把它“说明白”。1993年,经过3年时间的写作,《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出版。这本书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仅有20多万字,但在读者中收获了热烈的好评,被国家五部委评选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之一,同时入选的图书还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
自这本书之后,武斌正式将研究领域转向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当时还没有‘文化自信’的说法,但我已经注意到了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应该把中华文化放到更广阔的世界文明的坐标中去审视,这样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可以更深刻、全面。”武斌说,这次出版社的约稿让他发现了一座无比广阔的学术富矿,进入一个无比广阔的文化世界。

武斌
一本写了30多年的书
从近200万字到480万字
面对一个全新的学术课题,不仅没有学术成果可以借鉴,还面临着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双重挑战。
“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天天跑到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记笔记,做一些扎实的基础资料积累工作,进而梳理出线索和层次。”武斌说,仅读书笔记他就写了十几本。
1998年,近200万字、三卷本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正式出版,这本书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也奠定了武斌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
但武斌仍不满意,认为其中的一些论述不够深刻和全面。所以在这本书出版后,武斌仍然不间断地收集资料。“看书、看材料,特别是最近这20年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很快,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更多新材料被‘发现’或者翻译到国内。”武斌说,这让他的学术更新有了资料基础。
2012年,在退休的第二天,武斌就开始动笔,重新梳理书稿,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进行大规模修订,不仅增添大量新内容,更对全书的架构、脉络和叙述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2021年,480万字、六卷本《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受到学术界、出版界乃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认为,该书采取长时段大历史的叙述方式,以现代的全球化、世界化的学术眼光,把中华文化置于世界文明的总体格局之中,全面论述了从文化的发生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全过程;论述了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向海外不同地域传播的载体、形式、内容、过程,以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地位和影响;论述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化体系的规律和条件,阐发了走向世界的过程对于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意义。
此时,距离武斌涉足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这一领域,已经过去了30多年。
一次任职经历
打开更加辽阔的学术视野
翻开武斌的履历,还有一段特殊的“博物院院长”经历。
2004年10月,武斌从辽宁社会科学院调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担任院长期间,武斌提出建设“研究型博物院”办院方针,把学术研究作为博物院的工作核心,以学术研究统领博物院的业务工作,创办了《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沈阳故宫博物院年鉴》等出版物。此后,还出版《沈阳故宫四百年》《故宫学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论》《沈阳故宫博物院》等专著,主编《多维视野下的清宫史研究》《沈阳故宫与世界文化遗产》等。
“我在博物馆里工作,每天面对的就是过往历史的‘现场’,这对我理解历史非常有价值。”武斌说,由此历史不再是文献上一段段文字,而是一个个生动的场景。
同时,通过馆际交流,武斌也实地走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遗迹。“能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些历史现场看一看,和海外汉学家做深度交流,极大提升了我的学术修养,学术研究的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武斌说。
2012年,从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岗位退休后,因为有前期丰厚的积累,武斌迎来学术爆发期,仅2024年就已出版7部著作。在《重回1500—1800——西方崛起时代的中国元素》中,武斌依托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图像史料,展现了16—19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风”,呈现了许多历史细节和宝贵资料,重新探寻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篇章;在《江河万古流——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中,武斌从史实出发,深入剖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探究这些特性形成的根源及其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挖掘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传统,寻找潜藏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密码;在《丝绸之路文明史》中,武斌着重论述中国各个朝代对丝绸之路的经略和管理,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为读者呈现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中外文明交流史;还有受到各界高度好评的姊妹书《西方典籍里的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与认知》和《中国典籍里的西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认知》,两部书以典籍为客观依据,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深刻探讨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世界识见照进中国的历史进程。

书架上的《丝绸之路文明史》
目前,关于中华文明的研究,武斌已出版专著60余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多年学术活动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这一领域,便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徜徉,其他研究和著述,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武斌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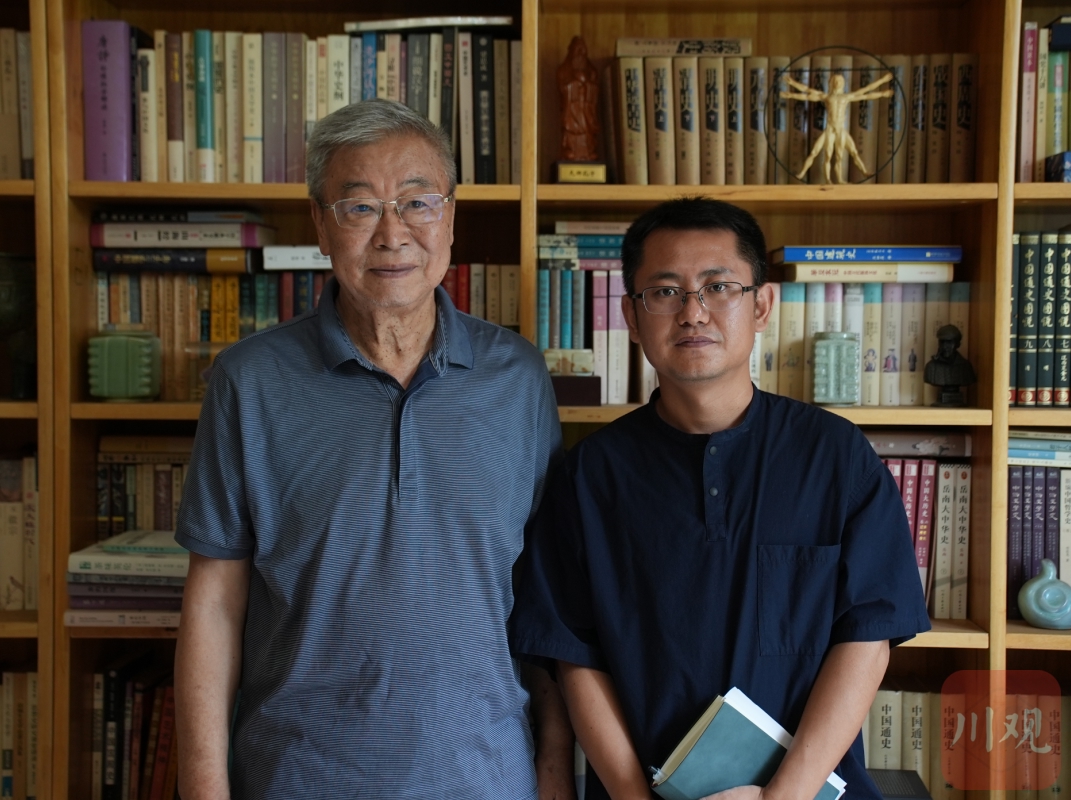
武斌(左)与川观新闻记者(右)
对
话
以全球视野来“回望”中华文化
通过“他者”眼光来认识自己
记者:您一直倡导要以全球视野“回望”中华文化,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明有怎样的意义?
武斌:对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了解,会更全面、更深刻,会更加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要文化自信,首先要文化自知。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两个路径,一是从我们本身来认识,从史书记载到考古发现,这些都是认识中华文化的线索。但这还不够。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世界文明中孕育和发展的。我们看到,两千多年来,西方的典籍在不间断地记录中国,记录中华文化。通过这些文献典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在他人眼中的样子,看到我们在世界的形象。这些记录和书写,有客观叙述,也有热烈赞誉,还有尖锐批评。赞誉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在与西方文明作比较。他们是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下与西方文明作比较来评论中国的,有自己的“期待视野”和“文化眼镜”。阅读这些记载中国和中华文明的西方文献典籍,也是我们通过“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的过程。这样,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来自我们对自身悠久历史文明的认识和体会,也来自对我们的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贡献的了解和认识,来自对中华文明的世界形象的了解和认识。
换句话说,追寻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在追寻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我们看到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产品是全球贸易的大宗,中国技术是全球交往的重要力量,中国元素成为欧洲的新风尚,中国思想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源泉,中西方从物质领域的交换和交流,发展到艺术、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与互鉴。因此,我们必须超越本国、本民族,以全球视野来“回望”中华文化。
中西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记者:您的新作《西方典籍里的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与认知》和《中国典籍里的西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认知》这两本都很有趣。中国和西方,在对方典籍里分别是如何被呈现的?
武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两本书里都有一个“想象与认知”的副题,说明双方对彼此的认识都是一个从最初雾里看花的奇异想象到逐渐丰满的过程。
我们先从西方看,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对西方的生活、经济产生影响。当时他们对丝绸十分好奇,以“赛尔”(Ser)即汉语“丝”(si)的发音来称呼丝绸,以“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国”,来称呼生产丝绸的国家,但具体这个国家在哪里、什么样他们不知道,只是说“赛里斯人”居住在“东方的边缘”,这是西方对中国的早期想象之一。
此后,西方人一直在寻找“丝绸之国”。元朝时期马可·波罗因为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他的游记对西方人认识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航海后,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通过一部部著作、一封封长信,源源不断地将在华见闻和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呈现在欧洲读者面前,大大丰富了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为中华文化的西传起到了积极的媒介作用,其中像利玛窦、汤若望等很多人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如此,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不再是通过种种传闻获得的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土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从中国来说,早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同样夹杂着许多想象和传闻。比如《山海经》中很多记载,就反映了上古时期华夏族群对地理空间的想象和认知,里面的“四极八荒”成为当时人们构筑世界观空间秩序和异域想象的基础。
“西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交通的逐渐发达,中国人所说的“西方”也是不断延伸、不断变化的。秦汉及以前的“西方”,主要是指“西域”,即中亚一带。到唐朝时,中国人所说的“西方”主要是指印度河中下游和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元代,在中国社会文化舞台上,活跃着很多“色目人”,其中大部分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充当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
明初时郑和所“下”的“西洋”,指的是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的海域和国家,这是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到达最远的“西方”了。晚明时期,欧洲传教士来华后,为了与中国人心目中指称印度、阿拉伯等为“西方”的传统意义相区别,他们自称为“泰西”“大西”“远西”“极西”,以示其所在的国度和地区才是真正的“西方”。到了清代,中国人世界观念里的“西洋”和“西方”指的就是欧洲,此后又加上了美洲,这就是我们今天通用的“西方”概念了。
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人主动去认识世界,主动走向世界。历代中国先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畏艰险,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了自己民族生活之外的世界。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人们相遇、相识,接触了许多奇异的风俗与文化,看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奇珍异物,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和经验。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东西方一直互相寻找、了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记者:在中西方互相寻找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奇妙的“相遇”。
武斌:这里既有大的文化相遇,也有很多“君子之会”。在17—18世纪,中华文化与启蒙运动的相遇,是一次伟大的文化际遇。这期间,中华文化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等诸多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智活动,对西方新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都在自己的著作里留下对中国的诸多论述和评论。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也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接触、碰撞,都曾给对方深刻的刺激和影响。
对于“东西君子之会”,我写过一个系列,聚焦研究中西方互鉴过程中的一个个人物。明末清初,欧洲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都非常有学问。比如,伽利略的学生汤若望,他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那个时期很有趣的一道文化风景。意大利人利玛窦和明代人徐光启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文化事件。再比如,英国作家毛姆与中国学者辜鸿铭的会面,也是中西文人之间交往的一个趣话。
正是中西之间一个个“人”的相遇,推动了中西之间文明的交流。
高势能文化吸引全世界关注
记者:中华文化为何能走向世界,并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武斌: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国力。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出现过几次非常耀眼的传播高潮,其共同特点和规律是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和平发展的时期。汉、唐形成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大帝国,元朝更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而至明清之际,特别是康乾盛世,更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高峰。国力强盛带动当时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创新和进步,由此出现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高势能文化必然吸引来自全世界民众的关注,并主动前来中国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积极向优秀文明靠拢。历史上,中华文化以其凝聚力和辐射力,形成了以中国本土为根源,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及其特殊的文化秩序,一直存续到19世纪,而其影响则延续至今。
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华文化自身来说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先,在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面,例如丝绸、瓷器、茶叶三大物产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产生多方面影响。
其次,在于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以耀眼的光芒吸引海外关注。而且,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居于世界之先,而是整体性地领先于世界。
再次,还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态势、文化传播和输入机制。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去了解世界
记者:从您的研究角度看,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何在?
武斌: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注重传承的自觉意识,也具有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博大的胸怀,努力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文化,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各家思想的交锋与激荡,诸子之间相互借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由此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根脉。
直至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鸦片战争及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给中国造成了重大的文化危机,促使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走上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而痛苦的过程。
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出现了后人称之为“开眼看世界”的努力。而到了19世纪末,又有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去看世界,除了带回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带回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受。
“变局观”与世界意识,是中华民族能够走出近代以来的危机和困境,使中华文化得以实现自我再造和更新,并且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形式获得新的强大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以积极的心态“走出去”,以开放的心态“引进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世界眼光,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与时俱进的能力,始终与时代同行,这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记
者
手
记
书房里的中西方交汇
武斌教授的书房位于远离沈阳市中心的一个小区。或许是一种巧合,书房距离沈阳的母亲河浑河很近。千万年来,悠悠浑河浇灌出灿烂的辽东文化,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浑河沿岸就有人居住,此后中原文明和辽东文明不断在这里交汇、交融。
武斌的书房,正像是文明长河中的一处节点,中西方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交流后,在这里再一次“相遇”,并产生新的学术命题。
书房里面存放了他多年来搜集的2万多册图书资料。正是在这间书房里、在武斌的笔下,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逐渐明晰。武斌说,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他希望能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武斌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在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写作一些简明扼要的“小书”,比如《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简史》《丝绸之路简史》,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二是开展一些细分专题的研究,以发掘和总结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原因和规律。
武斌透露,他研究“文化摆渡者”的专著即将出版,书写的是那些在中国生活过、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的西方人。
事实上,武斌自己也参与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之中。他1991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一书,后来由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教授阿齐兹翻译,畅销阿拉伯世界。
“东西方文明相遇时的碰撞、影响与互动,成就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武斌说,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还需要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策划:李鹏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四十八期
执行:黄颖
记者:王国平
摄影:韦维
海报:刘津余
编辑:杜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