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辉
在这个信息繁复的时代,人们往往渴望在心灵深处寻得一片宁静之地,那里没有城市的浮华,只有自然的纯净与乡村的质朴。诗歌,作为人类情感与智慧的结晶,正以一种全新的维度,引领我们走进自然,走进乡村,聆听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激发读者内心深处的思考与共鸣。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吕煊诗集《乡村新物语》打开了诗歌的新维度,即自然物语与乡村应答的心灵通道。
自然与乡村,是诗歌永恒的灵感源泉。在吕煊笔下,山川湖海、花鸟鱼虫,皆能言说,皆含深意。它们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景物,更是生命哲学的载体,是宇宙真理的隐喻而乡村是诗歌情感与记忆的归宿,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一种自然的附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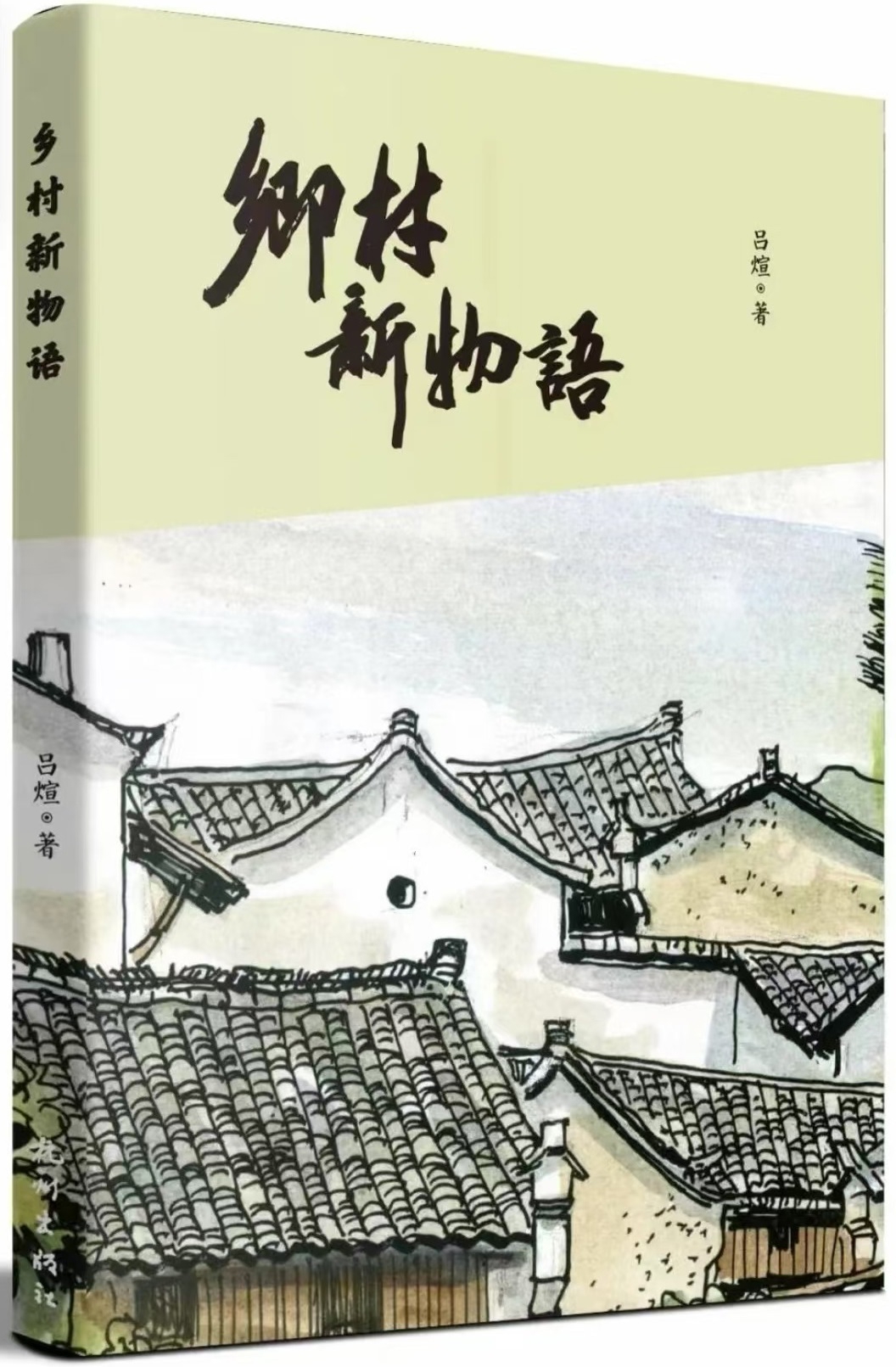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乡村新物语》里,那些自然场景、乡村原像不间断地呈现出崭新的诗歌维度与精神图谱。说到底,这是一个写作者对自然、乡村、社会、时代的身份认同与精神认同。这种认同感,无不维系着对自然的人世隐喻与乡村的精神景深的双重思考。
自然与乡村:一个互鉴的同构整体
自然与乡村,这两个看似独立又紧密相连的实体,自古以来便编织着一张复杂而微妙的同构关系网。回溯至遥远的史前时代,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源泉。森林提供庇护,河流滋养生命,山川勾勒壮丽。每一缕清风、每一滴雨露,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
在吕煊笔下,自然与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共同体。在《乡村新物语》里,他总在不经意间,将我们的思绪牵引至那片遥远而亲切的乡村——一个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地方。乡村,不单单是人文的载体,也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实体。
在集子里,山川与农舍、田野与炊烟、林木与飞禽,同构于一幅幅和谐安宁的画卷中。可以说,四季更迭,塑造了乡村独有的韵律与节奏,让乡村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而每个生命体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维系着这份和谐与平衡。
《跟随一只柿子来到峡口》就很有代表性:“柿子的香甜是史书上流传的/乡贤陈亮也曾云:方山柿,味如兰/柿子是有故乡的/她也历经了海外漂泊和回归/江山人陈荣是迎接她的王子/……为了一只柿子来到江山的秋垄/一只叫江峡秋王的柿子/是这个秋天最诗意的收尾”。
如果说,一只柿子,代表着乡村与自然美好的物象,那么,自然与乡村的关系,就像是被这只柿子所维系着的纽带,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不仅如此,吕煊身在其中,赋予一只柿子美好的化身,让它“行走”乡村,找到自然与乡村和谐共生的节奏与方向。
长期以来,关注于自然与乡村的同构,关注于自然的物语,成了吕煊诗歌显著的个性风格:意象简洁,节奏明快,穴位准确,把自然之光与心灵之光置入母语,照亮那些美好而令人纠葛的记忆。
《每一株植物都会拥有呼吸》就很典型:“那些植物和我的想像同步/多余的呼吸随时都会被终止/春天也会马上被改写”。当我们屏息静气感受每一株植物的呼吸,进入吕煊所描绘的自然与乡村同构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惊愕于吕煊从自然与乡村的物语中寻觅到自己的形象。很显然,吕煊把自然与乡村交织而成的物语当作洞察自然与社会的触角,从中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形象和偶然的感受。
不错,当自然之光与心灵之光一旦照彻在乡村场景时,吕煊总能迅即将其抽离为一个个关键语词,通过语义的重新编码,使之在互见、交集、对应的逻辑与情感演绎中,呈现出自然与乡村不可分割的光影。正如他在《木坦村在岩宕里静默》这样写道:“木坦村庄的印记镶嵌在岩宕的沉默里/它们是一株树上长着两朵不同的花”。
乡村与自然在同构中的相辅相成,代表着以自然万物为统领的生命意识的表达,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这样的自然法则,在《一棵千年柏树的多个侧面》中同样显眼:“遂昌龙洋群山包围的一个山村/我对一棵千年的柏树产生好奇/它的主干已被雷电击毁/露出折断的头/留存的高度似乎低于峡谷的风口/它看上去无比的坚毅和强壮/簇拥其下的旁枝散发浓郁的青草味”。
诗人描绘了被雷电击中的柏树,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脆弱。同时,当诗人以更宏大的视角关注自然时,又能感受到一种与《一棵千年柏树的多个侧面》不一样的、超越个体生命的宏大叙事。
以《怀念一株水稻》为例:“今天我冒着小雨重写水稻/是因为改写这个物种的朋友/人类和植物界的朋友/袁隆平先生他回归植物/他将灵魂留给人类/将肉身留给大地”。从“重写水稻”到“袁隆平先生他回归植物”,这样的同构关系,这样的情感跨度、思想跨度与精神跨度,让人思考起人类与自然、人类与未来的关系。
由此可见,吕煊总是在自然通道与乡村通道、生命通道与精神景深中或穿梭或逗留,用干净、简练、结实,有光泽度、画面感、形象感和节奏感的言语,诗意般地栖息其中,折射出一种浩然之气,这与袁隆平的人格魅力与卓著功勋相匹配。
吕煊对自然与乡村的书写,很讲究自然与乡村同构的可感、可听,这是他一直以来对自然对乡村书写的法宝。也许有人会说,可感、可听不就是回到视点与听觉了吗?其实,《乡村新物语》的可感、可听并非舶来品,而是特有的融时空、通感、气场为一体的思想通道、精神外观与精神景深。因为,他很讲究自然与乡村的内视点与回音区。
在吕煊看来,自然与乡村的共同体,就是要形成“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同构效果,正如《每一株草木都留给我安慰》,就是将草木与人类放在多变的环境里一次次地再生,使自然与人类有了同构关系的精神密码。
自然与乡村:一场未竟的物语对话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诗歌如同一股清泉,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当我们谈及诗歌的新维度时,不得不提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自然,以其无尽的奥秘与壮丽,向人类诉说着无声的物语;人类,以乡村作为媒介,回应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深情呼唤。
可以说,《乡村新物语》的诗歌新维度构成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自然的物语,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乡村的应答,让我们在守望中感受到自然的心跳。
当深入阅读《乡村新物语》时,不禁会思考:在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中,该如何平衡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关乎诗歌的创作与欣赏,更关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为此,吕煊以“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呈现诗歌的新维度,这不仅是文学上的探索与创新,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自然,是宇宙间最伟大的诗人。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四季更迭,每一处风景,每一声声响,都是自然赋予的诗意。而乡村,面对自然的物语,从未沉默,一场关于生命、和谐、未来的深刻对话,在自然这个大舞台亮相。它告诉我们,人类并非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谦卑的学习者与守护者。
《桂花只在河水里打了一个结》就是一个明证:“流淌了千年的河水,此刻/发出水声轻抚岸边的岩石/桂花放弃言说,满怀着喜悦/只是轻轻的在河水里打了一个结”。一首好诗,有时不因结构的廓大而宏阔,也不因为物像的细小而狭窄。这首诗好就好在将自然定格在特定的场景中,让落水的桂花回归生命的中心地带。很显然,从边缘到中心,从无奈之“落”到从容之“归”,好似流水与桂花心存默契。
好诗歌会说话,读吕煊的诗,就像是万物自然而然打开“心影”,与读者的情绪、情思、情势、情调同频共振。这些年,吕煊的诗歌创作,除在内容上依然秉持对自然、生命的尊崇与敬畏外,在语言表达上更接地气,更贴近当下语境。说到底,他的诗歌语感、语义、情怀、思想相互补充,形成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的有效串联,构成与自然、乡村、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
以《在地铁遇见怀抱向日葵的女子》为例:“在地铁我遇到了/这样一个女子和她的三朵向日葵/……车厢里的汗味被气流悬挂/那些踮着脚尖的人/他们无视这三朵向日葵/也无视有一个女人/抱着三朵向日葵/在午后乘地铁”。诗人的“有意”与众人的“无意”发生冲撞:向日葵、女子、汗味、车厢……交织在一起,因强烈的对比,交错出异样的感觉。吕煊抓住这个异样,引起人们的反思。
也许有人会问:这哪是乡村应答,这明明是城市应答。不错,与其说这是城市与乡村的间离,不如说这是乡村对城市的追问。这种借助乡野女子怀抱向日葵的悖逆式的乡村应答,不仅是对社会的换位思考,也是对社会伦理的自然回应。这样的回应,才能说到实处、思到深处。
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的新维度——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被赋予更深刻的含义。在新时代,诗歌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赞美与反思,更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审视与反思。同时,乡村作为连接社会与自然的桥梁,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中停下脚步,聆听自然的声音,感受自然的魅力。
《乡村新物语》正是通过乡村,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更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和谐与共生。自然与乡村,过眼烟云的往事并不鲜见,所匮乏的是情感储存、情感冲动、情感释放的驿站。凭借这个驿站,吕煊把自然中被遮蔽的事物带回人间,延拓了人间情怀的宽度和景深。
以《在富阳被一棵野菊拦住了去路》为例:“一棵野菊拦住了我的去路/庚子年往黄公望隐居的山野/放下身段其实也是一种幻想/几十年抄书的磨练对于绘画/只是从这个门到那个门/挡道的是另一个活在虚空里的自己”。
心之所至,万象为开。这首诗把自然的视界打开了,带领读者进入可思的空间。在吕煊看来,自然的物语与乡村的应答,并非一问一答的刻板哲思,而是两者在互动基础上的情思与自觉,是一条思想通道,即自然与乡村互动言语的气息与脉动。
说到底,吕煊致力于自然物语与乡村应答的生命自觉与精神自觉,形成自然物语与乡村应答的有效串联,避免思想大于形象。《干花,是美的另一种暴动》最具代表性:“有如干花,她曾经的怒放填满你的想象/深夜里你泪如满面地倾诉/给无边的黑,增添了厚度/美是天使,给了你毒的迷离/反复的距离永远只是一步之隔/干花复活/需要美发动一场战争酝酿一种暴动”。
当吕煊恍然领悟到诗歌再不是一股青春期的情绪释放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理念的转变、价值的转换,他从乡村经验与自然境遇中得到蜕变,且多了一层在场的、现实的、伦理的、生命的诉求,《干花,是美的另一种暴动》作为自然生态的极致表达,其复活、迷离也好,其怒放、暴动也罢,这一切源于吕煊苦苦追寻的内心秩序与生命应答。
同时,不管是探究自然原相,还是直面乡村百态,他都在技艺追求的过程中力图保证文本意义的高度完整,并对写作的题旨、构架和速度进行有效控制,从而避免乡村经验可能导致的乡愁式的低吟浅唱。
吕煊以简约、质朴的手法将自然物语、乡村应答与宏阔的社会背景融为一体,表现了一位成熟诗人的风格与底气。可以说,由于他熟练地掌握了“充盈的自然”与“殷实的乡村”相互渗透的表现手法,他的诗歌创作,不管是在场的,还是虚拟的,总是保持高度的热情,保持高度的平衡力。
当我们也像吕煊那样冥想“滴水的下落”,或仰望或俯视“那些短促的阳光和鲜草”以及探寻“虚幻的边缘覆盖了真实”,特别是“现在 夜雨在我的屋顶不停地跑动/温润警示血管的干涸”时,我们总是力图联想到与吕煊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乡村农舍。
这些地域属性与人文属性激活了他的创作灵感,调匀了他的创作激情,呈现出由外而内或由内向外的、物象与心象交叠而成的自然与乡村“回应对话”的场景。
《乡村新物语》的旨趣,就是要激发读者感知这一景观,使处于文本中心的“自然与乡村”能在自然之光与心灵之光相互交错中被人看见,被人听见,让读者感觉出“自然与乡村”因与永恒的事物有着同构关系而变得高尚。
总之,《乡村新物语》就是自然界最好的人世隐喻,承担了对自然界难于用言辞来解答的审美职能。说到底,吕煊正是凭借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将自己托付给自然所不能及的某种超现实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合成的、延续的、可感的人与自然同缘同构的美学体系。
(《乡村新物语》,吕煊著,杭州出版社)